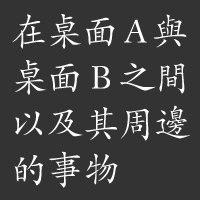
桌面A面積73吋見方,橡木面。
這桌面是在2003年自己動手造的。當時畫廊設在皇后西街一幢由糖果工廠改裝的建築物。2000年我們在這裡開業了小畫廊,畫廊不大,約900餘呎,分前後兩個空間。那時候,這個桌面便是放在向北有著大扇落地窗子的一方。桌面主要用來閱看照片,桌底的空間用作存放伺服器,打印機等硬件。也算是上下一個平衡罷。後來畫廊的空間又改動了少許,我把桌子移去接近入口也即是向南的一方。粱巨廷先生第一次來我們的畫廊,桌子便是這樣的擺放,他第二次來的時候我們已遷往了吉石大道50號。
我們是在2006年搬遷的。一幢三層高的建築物原是左右兩個相連的單位組成,我們將左右打通,地下用作畫廊,家居則在三樓。在三樓那較小的左邊單位我用之作為工作間。其實工作間只佔用了那邊三份二的空間,因為工作間後面便是我的臥室。
2006年初用這個工作間的時候,桌面A是放在向東近著一大扇窗。大約在2009年中,我把工作間的空間運用改換了少許,放桌子A的那邊轉爲放沙發。沙發對著一列由地面至天花的書架,左側即是大窗。大窗雖然橫跨了大部份的牆,但窗並不是落地而立,它大約是從地面之上兩呎許而建。窗下的空間我們怎得放過,又放了一列矮書櫃,眼看櫃的頂部不斷增加疊疊的書本雜誌,窗的領土已日見消瘦。
如果說這個工作間的平面如一個日字,那麼,是次的改動便是將桌面A從近東那方移去了近西的區域。桌的一邊靠著西牆,其他三邊卻是開放,即是可以在桌邊坐著或立著工作。這個工作間,四面都有自然光進入 - 除了東面的大窗,南面的窗子可外望Gladstone酒店及皇后西街,西邉即桌面A所靠之牆左有窗而右往後通往浴室及臥室。也即是說,下午時份,桌的西面左右皆有陽光從後方透進來。喜歡之極。北面原即是與右邊單位相連之牆,我們洞開了一廣四呎許無門之通口。通往那邊是居室飯廳等,此不細表了。
桌面A之右,也即剛才說的連著隣單位的牆,搬進來後我便造了一書架。書架拔地而起高及至天花,盡跨牆左右之極。書架不深,約八吋許。也即是說只容放某類較小本的書。書架每層相隔不一,書本皆以高度為分類。此種改寫圖書館管理學的方法,優點是擁有港式空間使用術的傳統。全棚書架都填滿了,不留它一點空間。
桌面A上面吊著一方42吋乗42吋燈罩。Broncolor 之HAZYLIGHT也。後70年代我們起步從事職業攝影,第一件燈光器材便是買了這件行內頂尖好物。Broncolor 著名的色溫感,HAZYLIGHT提供有性格的光源。光源的性格決定於反光罩內部反光面的設計,HAZYLIGHT的光質柔和,光朿卻是直出而不是擴散,也即性格之所在。HAZYLIGHT與我們相伴30餘年,今天我們再也不需要Broncolor的著名色感相助,替代閃光燈用的卻是一枚23W(相等於傳統燈泡100W)的省電燈泡。
事實上我們仍在整理從香港輸運過來的舊物。去年秋天,我從地庫把一張裝裱在鐵銹金屬框的照片移至工作間,靠放在桌面A背西之牆。數天前黃少儀來訪談,她想知道多一點關於香港70及80年代設計行業的事情。我們不期然談到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的成立日期。剛才說的那張照片便是在公會成立後第一次會員展覽而做的。大概應該是在1990年罷。
照片44吋乗56吋橫度,右方有斗大「廣進」二字。原是來自新年揮春之「財源廣進」,當時只取廣進而棄掉財源想來也頗吻合潛意識。廣進又有如電腦平台的開放碼,萬事如貫魚來八方。印象中這張照片,當時正要替中文版的流行通信做一張關於五六十年代的拼貼,這張照片算是另外版本的副產物。值得一提的是背後密麻小字乃來自香港六十年代華僑日報的電台電視節目表,當時報內每天均以全版刊載。試抄寫我照片左上角的一段內容:十一時,新聞簡報,今日賽馬最後貼士報導,粵曲,牡丹亭之西樓驚夢(任劍輝),三十分,倫理小說「恩仇美卷」。十二時,新聞簡報,港九時事,三十分,奇情小說「愛情狂想曲」。
開始的時候,我的電腦工作都是在桌面A進行,正中放著27吋的偌大顯示屏。去年中作了小改動,電腦硬件圴移至向南的桌面,桌面A便成了書本,照片,印刷物的沙流地。
桌面B是一塊白色的雲石板,有灰色抽象雲紋。四面已打磨成半圓邊。現在的工作間,桌面B剛好是沙發與桌面A兩個空間的分隔。雲石板闊27吋橫62吋,右邊張開半圓。這桌面原是於八十年代為拍一張廣告照片而訂造的道具。也隨家搬過不知多少回。199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提過常常在這張半圓的雲石桌面與妻共喝紅酒談天,20多年後我們也是常有此習慣。此外,我們也常在這桌面吃水果,橙汁西柚汁等酸性物料在雲石表面留下斑斑的痕跡。歷史罷。我也不甚著意的去把它打磨光滑。
繞了一個圓周本來是要介紹桌面A與桌面B出場作個白描,不料連綿瓜藤細數細碎竟然去了一大片篇幅。最近與又一山人開始了一項關於創作的對談,我在最近一貼提到過去所走不同的路如何正是影響著今天的種種。也是如此,這些桌上痕跡如何爲今天桌面A與桌面B的行雲流水提供註腳。
2010年秋天我開始了PostscriptX,一組彷如日誌的攝影。今年一月底開始的「在桌面A與桌面B之間以及其周邊的事物」也可算是一則姊妹篇。前者用主觀的方法(或角度)去記事。後者則採用客觀的角度去記錄一個主觀鎖定了的空間。照片都是隨意,也不講究。桌面A與桌面B東西交通,也記錄著我與黃楚喬日常的瑣碎閱讀,圖書館的書,朋友的書,朋友的畫稿,也有紅酒濃茶花生米。也是無敘事的小說體裁,也是無韻律的報導文學。
對我來說,照片常常是一項表達。是故,記錄的成份明顯縮少了。我又想過到底記錄是個客觀還是主觀。後來我否定了前者,那麼,主觀的記錄已不是真正的記錄了。那只是利用記錄的途徑去達致一項主觀的表達。其他的只是形式問題。
雖然,「在桌面A與桌面B之間以及其周邊的事物」在我來說仍是一則思考的過程,但也還是可以作這般的理解。拍攝這些照片,我用的是Sony NEX5照相機,轉配Canon FD 14mm f2.8 L鏡頭。轉換後也即涵蓋面約90度。順記。

點擊覽閱全組照片
「在桌面A與桌面B之間以及其周邊的事物」
http://leekasing.com/table
「在桌面A與桌面B之間以及其周邊的事物」2011版,包括2011年1月至12月間上載之照片逆序
